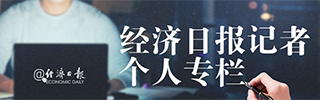未成年人保護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了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位一體”的新時代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其中,學校保護是重要一環。學校作為教育機構,承擔著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和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管理行為。同時,根據《教育法》《民法典》等相關規定,學校對在校未成年人承擔教育管理和安全保護的職責,未盡到上述職責的,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為切實發揮司法裁判規范、評價、教育、引領功能,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選取五件典型案例予以發布。
案例一
小學生在校受傷,學校并非
必須擔責
——趙小某訴某學校侵權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某日放學時,12周歲的六年級學生趙小某自教室下樓行至教學樓三樓與二樓樓梯間平臺時,從樓梯臺階上摔倒,帶隊老師隨即聯系家長并陪同送醫。經診斷,趙小某牙齒受損、嘴唇挫傷擦傷,門診治療及復查后,醫囑建議為18周歲后牙樁冠修復。
趙小某以學校在放學過程中未有老師在教室至校門路段組織秩序,存在監管不力為由,訴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學校賠償醫療費、營養費、精神損失費等合計8萬元。
裁判結果:審理法院認為,根據現場勘驗結果及證據,趙小某摔倒受傷并非樓梯等設施場所本身缺陷導致。學校已多次對學生進行了校園安全教育宣傳,樓梯、墻面等地方張貼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標志,盡到了學校的教育職責;在趙小某受到損害后,學校亦及時采取了通知家長、陪同就醫、調查事發經過等措施,履行了學校必要的管理職責。趙小某及其法定代理人應對學校未盡教育、管理職責承擔舉證責任,現其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學校存在過錯,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據此,審理法院判決駁回趙小某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校園傷害事件中認定侵權責任,不能僅因事故發生在校園即認定學校一定具有責任,而是應當結合未成年人受傷害原因、學校是否已進行常態化安全教育、相關場所設施有無醒目的安全提示標志、事發后有無在第一時間通知家長并陪同就醫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避免產生“學生在學校受傷,學校必然擔責”的錯誤認識。本案裁判貫徹了“依法引領校園保護”要求,運用“小案例”闡釋“大道理”,充分發揮了司法引領良好社會風尚的重要作用。
案例二
學校未及時發現并制止校園暴力行為,需要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侵權責任
——張小某訴蔣小某、某中學等健康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張小某、蔣小某、王小某均系某中學八年級學生。某日課間休息時,蔣小某與王小某發生口角爭執,蔣小某將王小某擊倒在地后又騎坐在王小某脖頸處,持續用拳擊打王小某。張小某路過此處,見一旁的教師休息室內沒有班主任老師,便自行上前試圖將蔣小某拉離。蔣小某突然回身,揮拳擊中張小某左眼。后某中學將張小某送至醫院救治。經鑒定,張小某左眼外傷,構成人體損傷十級殘疾。張小某訴至人民法院,要求蔣小某及其父母、某中學賠償損失共計21萬余元。
裁判結果:審理法院認為,本案侵害事實由蔣小某直接導致。事發時,蔣小某作為一名八年級學生,應當具備一定的辨別是非和控制情緒的能力,卻在課間對同學實施毆打,并對出面勸阻的張小某揮拳相向,行為沖動,未計后果,對損害事實的發生具有主要過錯,因蔣小某系未成年人,故由其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張小某面對校園暴力,能夠出手制止,幫助同學,不僅并無過錯,還應予以褒揚。蔣小某因瑣事在課間休息期間毆打同學,該毆打行為持續期間,有數名學生圍觀,未有老師發現并予以勸阻。某中學作為專業的教育機構,沒有針對本校學生的具體情況,對課間加以必要的嚴格管理,也沒有密切關注學生動態,沒有做到及時發現和防止學生間的沖突加劇,以致發生本案的后果,故某中學在履行教育管理職責時存在不足,亦應對本案的后果承擔一定的責任。
綜合當事人的過錯程度、致害原因及本案實際情況,判決蔣小某父母承擔70%的賠償責任,某中學承擔30%的賠償責任。
典型意義:校園暴力行為會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學校作為防控校園暴力的重要一方,需建立嚴格的監督和反饋機制,遏制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本案中,學校未及時發現并制止發生在學校走廊的毆打行為,學校的安保措施存有漏洞,應當視為學校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對于受害方遭受的各項損失,學校需要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本案通過司法裁判,進一步明晰學校在校園暴力事件中的責任邊界,督促學校建立有效的校園暴力防控機制。同時,對未成年人制止校園暴力的行為予以正面評價,體現守望相助的價值導向。
案例三
中學生課間踢球意外受傷時自甘風險原則的適用
——林小某訴陳小某、某中學等健康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林小某是某中學高三年級學生,陳小某系該校高一年級學生。某日午休期間,林小某與陳小某在學校操場參加由學生們自發組織的足球活動,二人分屬不同隊伍。林小某接到傳球后快速帶球從右側進攻,倒地鏟球時與防守的陳小某接觸,林小某倒地受傷。林小某認為其被陳小某踢到受傷,某中學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遂以陳小某及其監護人和某中學為被告訴至人民法院,要求陳小某及其監護人、某中學共同賠償損失59萬余元。
裁判結果:審理法院認為,林小某與陳小某等人正在進行的足球對抗比賽多人參加,具有群體性、對抗性,并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險性,屬于“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林小某事發時年滿17周歲,陳小某事發時年滿15周歲,二人均參加過規范的足球訓練,具有多年踢球經驗,對于參與足球運動潛在的危險和可能的損害理應具有預見和認知的能力;本案所涉足球活動系學生自發組織,林小某、陳小某自愿組隊參與意味著自愿承受足球活動可能導致的損害后果,因此可以認定林小某參與案涉足球活動屬于自甘風險行為。本案中,林小某快速跑動中倒地觸球將自身置于危險之中,與上前防守的陳小某相接觸,陳小某并無加速、踢踹、動作過大等明顯違反足球規則的動作,因此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陳小某在損害發生時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故陳小某監護人對于林小某所受損害不應承擔侵權責任。關于某中學應否承擔責任。事發時林小某已滿17周歲,系在午休期間與同學自發踢球受到人身傷害。經查,某中學足球場驗收合格,日常教學活動中重視法治教育,給學生以安全提示,事發后配合林小某解決相關事宜。故某中學盡到了教育管理職責,不應承擔侵權責任。綜上,審理法院判決駁回林小某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規定:“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活動組織者的責任適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條的規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高中生系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相較于初中生及小學生,對于經常參與的日常體育活動可能的風險已經有較為清晰的認知,本案適用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規定的自甘風險原則,強調參與者對于風險的預判,有助于提示高年級學生注意預防體育活動給身體造成損傷的危險。同時,本案中足球比賽系學生自發組織,學校不屬于活動組織者,故不適用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而是適用第一千二百條規定。本案根據各方提交的證據,具體分析學校有無盡到教育、管理職責,避免過分苛責學校,從而倡導學校鼓勵學生課間自由活動,引導未成年人在校園內健康快樂成長。
案例四
學校不因實施合理的教育懲戒行為而承擔侵權責任
——李小某訴某學校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李小某為某學校一年級學生。某日,因李小某在校期間扎、咬其他同學,某學校老師在放學時間與涉事家長進行溝通,并在班會上讓李小某向其他同學道歉,因李小某態度不誠懇,再次要求李小某鄭重道歉。李小某監護人認為某學校老師當眾指責李小某、不聽李小某解釋、無理要求李小某當眾反復道歉,造成李小某心理嚴重傷害,致使李小某持續情緒低落、無法正常返校。經多次交涉無果,李小某將某學校訴至人民法院,要求某學校賠償損失2萬余元。
裁判結果:審理法院認為,某學校老師批評并要求李小某向同學道歉的行為,屬于教師正常行使教育懲戒權,本案現有情形不足以證明某學校對李小某的管理行為存在超越或濫用教師教育懲戒權的情形,故判決駁回李小某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教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學校對受教育者有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的權利。”202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亦規定:“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學校和有關部門要依法保障教師履行教育職責。”同時,教育部發布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第八條明確規定了教師在課堂教學、日常管理中,對違規違紀情節較為輕微的學生可以當場實施“責令賠禮道歉、做口頭或者書面檢討”等教育懲戒。本案中,老師要求李小某向其他同學當眾賠禮道歉未超出合理的教育懲戒措施范疇。本案依法作出相應判決,對于支持并保障學校依法履行教育管理職責,規范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等各方行為具有重要的規則引領和示范意義。
案例五
家長以監督為名虛構事實詆毀學校的應承擔侵權責任
——某小學訴張某某網絡侵權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張某某的兒子在某小學就讀。張某某認為其兒子在校期間,學校教師存在霸凌、孤立行為,遂不斷在多個社交媒體發布文字和視頻,控訴某小學的教師孤立、霸凌孩子,及該校存在權錢交易、違規招生、迫害優秀教師等情況,言辭激烈且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某小學認為張某某虛構事實,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具有明顯誤導性,嚴重侵犯某小學的名譽權,遂以張某某為被告訴至人民法院,要求張某某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某小學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出的合理費用。
裁判結果:審理法院認為,張某某在公開社交媒體平臺發布針對某小學的文章與視頻,具有明確的指向性。之前經張某某多次投訴,校方、教委進行調查核實后,張某某所反映的問題不屬實。訴訟中,張某某亦無其他證據證明某小學存在張某某所稱的行為。故張某某通過網絡公共平臺發布包含侮辱性言辭的涉案內容,且對于言論中涉及的內容未能提交證據證明其客觀真實,構成侮辱誹謗。該內容被廣泛瀏覽傳播,勢必導致某小學社會評價降低,侵犯某小學名譽權。綜上,審理法院判決張某某向某小學書面賠禮道歉,并賠償相應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
典型意義:《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規定:“民事主體享有名譽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家長作為孩子健康成長的第一責任人,具有對學校教育方式與教學內容進行合理監督及合法維權的權利。但是,當家長不認可學校的教育方式與相關部門的處理結果時,應當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保證所述內容理性、客觀、真實,不得侵犯他人名譽權。本案明確了家長對學校管理教育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邊界,對于構建良好家校關系具有引導意義。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
(審核:歐云海)